2025年10月17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邀请到希腊国家研究基金会(National Hellenic Research Foundation,NHRF)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知名科学史家埃菲思缪斯·尼古拉耶迪斯(Efthymios Nikolaidis)教授在人文楼B206举行讲座。本次讲座标题为“公元17—19世纪欧洲科学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The Spread of European Science in the Ottoman Empire, 17th—19th c.),由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主持。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王哲然副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鲁大龙教授,以及来自清华大学及北京周边大学、科研院所师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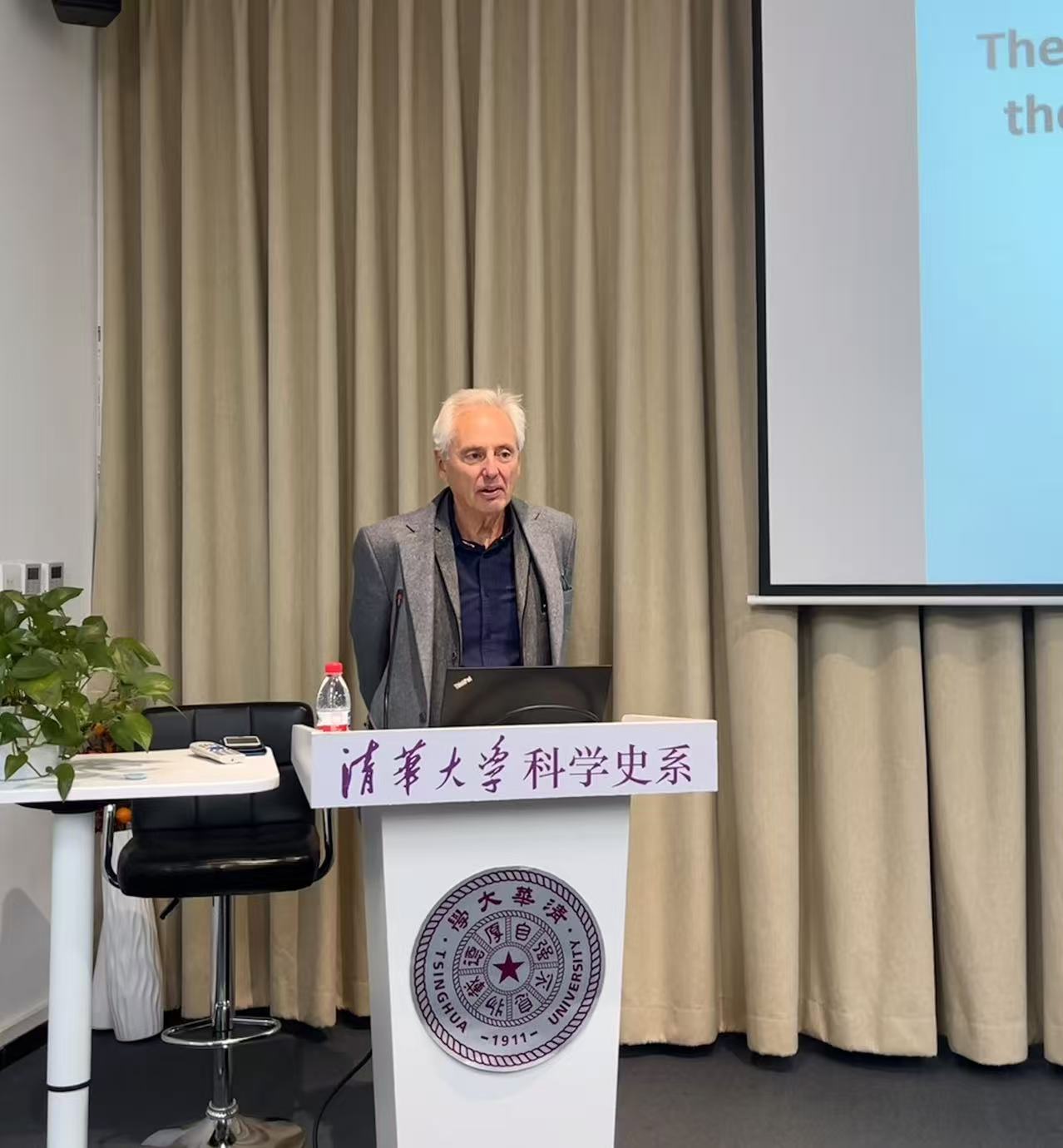
作为背景补充,尼古拉耶迪斯教授首先指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各宗教团体内部自治的“Millet制度”,从而导致了不同宗教信仰的分离局面。作为第一任希腊正教“Millet”总主教的艮纳迪欧斯二世(Gennadios II Scholarios, Γεννάδιος Β' Σχολάριος)于1454年删除了总主教学校课程中的科学内容而重视神学,造成了希腊正教区人文主义时代的终结;而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则在清真寺所办的“马德拉沙”(Madrassa)学校接受宗教教育,其中少量的“马德拉沙”会提供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科学的科学教育,但它们所用的教科书自16世纪到19世纪始终未见显著更新,直到1831年出现首个进入欧洲大学的穆斯林学生,现代科学才开始进入奥斯曼帝国。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个发生于意大利的传统:1670年,尼科拉欧斯·格吕曲斯(Nikolaos Glykys, Νικόλαος Γλυκύς)在威尼斯开设了最早的希腊语印刷厂,甚至比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希腊语印刷厂(18世纪出现)还要早。尼古拉耶迪斯教授将威尼斯的希腊语知识传统追溯到了15世纪的拜占庭人文主义者、枢机主教贝萨里翁(Bessarion, Βασίλειος Βησσαρίων)。贝萨里翁曾学习哲学、天文学,拥有大量藏书。他于1468年捐赠给威尼斯的约900册希腊语抄本,后来成构成了圣马可图书馆的核心馆藏。围绕贝萨里翁及其希腊语书籍收藏,意大利各地逐渐形成了多个希腊语学者圈,吸引了奥斯曼帝国学者前往,其中包括由希腊人文主义者伊阿诺斯·拉斯卡瑞斯(Ianos Laskaris, Iανὸς Λάσκαρις)1514年组建的罗马希腊语学院,以及希腊律师托玛斯·弗兰吉尼斯(Thomas Flagginis, Θωμάς Φλαγγίνης)1640年左右在威尼斯捐资兴办的正教学院等。
这些希腊语学者圈最终促成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内正教学者的聚集,后者将为现代欧洲科学传播到奥斯曼世界提供契机。尼古拉耶迪斯教授指出,奥斯曼帝国彼时还没有任何大学,而帕多瓦大学的国际化环境吸引了不同地域与宗教信仰的学生,许多富裕的希腊正教家庭会将男孩送到帕多瓦学习。于是17-19世纪的帕多瓦大学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希腊语教授与学生,如医学教授革欧尔吉欧斯·卡拉法忒斯(Georgios Kalafatis, Γεώργιος Καλαφάτης)、希腊第一任总督伊欧安内斯·卡珀迪斯特瑞阿斯(Ioannis Kapodistrias, Ιωάννης Καποδίστριας)等。
当视野转回奥斯曼帝国国内,尼古拉耶迪斯教授提请我们注意上述与意大利的交集为希腊学者接受西方世界(以及阿拉伯世界)对亚里士多德的重新阐释提供了契机,使得奥斯曼帝国希腊正教“Millet”内部的科学共同体重建进程得以从16世纪起缓慢开始,并在18世纪(启蒙时代)获得一定成果。其中总主教曲瑞珥洛斯·路卡瑞斯(Cyril Lucaris, Κύριλλος Λούκαρις)是一位重要的改革者。接受过帕多瓦大学教育的他,希望能够在奥斯曼帝国正教徒中重建古希腊文本与科学教育,为此任用了同样有意大利学习经历的朋友忒欧菲洛斯·科律达珥勒乌斯(Theophilus Korydaleus, Θεόφιλος Κορυδαλλεύς)教授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地理学与天文学),此举还招致了正教会内部的保守圈子的反对。尽管如此,正教会还是最终采纳了科律达珥勒乌斯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即应该从神学中分离出哲学以解释世界。尽管科律达珥勒乌斯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并没有为奥斯曼帝国带来现代科学,但尼古拉耶迪斯教授认为这一重要的“新人文主义运动”助长了科学教育事业本身,也增进了奥斯曼帝国与意大利希腊语知识传统的联络——在17世纪30年代至17世纪末期间,在奥斯曼帝国至少新建了12所希腊语学院,而这一数据在18世纪又有了显著的提升。
日渐发达的科学教育网络,开始催生首批向奥斯曼帝国引进新的欧洲科学的希腊学者。最早传入的“新科学”包括哥白尼新天文学体系、伽利略借助望远镜实现的天文新发现与哈维新解剖学发现等,但始终受到教会的限制,只有片段的提及而未见系统的引进。尽管耶稣会的科学传教并没有在奥斯曼帝国获得成功,但当时广泛的耶稣会科学活动也在辗转间令部分希腊学者接触到了更广阔的新科学世界。1707年成为新任耶路撒冷总主教的希腊学者克律珊托斯·诺塔剌斯(Chrysanthos Notaras, Χρύσανθος Νοταράς),就曾在1692年于莫斯科访问期间获得了俄国外交官斯帕法里(Nicolas Milescou Spathary)从北京获得的耶稣会天文学著作手抄本,其作者正是比利时籍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从中可以设想一条“北京-莫斯科-君士坦丁堡”知识传播脉络。克律珊托斯接受新欧洲科学的另一条途径来自巴黎,当他1700年访问巴黎时,巴黎的一批自由主义神学家以及巴黎天文台时任总监卡西尼(Jean-Dominique Cassini)对他进行了款待。1716年,克律珊托斯在巴黎出版了希腊语著作《地理与天球导论》(Introduction in Geography and Sphericals, Εισαγωγή εις τα γεωγραφικά και σφαιρικά),介绍了哥白尼、开普勒与第谷等人的天文体系,对后世希腊语学者接触新天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古拉耶迪斯教授引用了一段克律珊托斯的原话,足见其对于新欧洲科学的态度:“人们以前总说,在希腊人之中,除了雅典人之外的都是蛮夷。那么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荷兰人们都是蛮夷民族。可当他们接纳了雅典的智慧,当他们建起了科学院、体育馆和学校,蛮夷也变成了雅典人,反倒是失去一切的雅典人成了蛮夷。”
尼古拉耶迪斯教授继续介绍了一系列18世纪奥斯曼帝国接受新欧洲科学的新进展,如笛卡尔-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美托迪欧斯·安特剌奇忒斯(Methodios Anthrakites, Μεθόδιος Ανθρακίτης)所著的数学教材、厄乌革尼欧斯·布珥伽瑞斯(Eugenios Voulgaris, Εὐγένιος Βούλγαρις)在宗教圣地阿索斯山办学教授牛顿科学、尼刻佛若斯·忒欧托刻斯(Nikephoros Theotokis, Νικηφόρος Θεοτόκης)在科孚岛的教学活动等。虽然帕多瓦大学经过1715年开始的教学改革已逐渐将亚里士多德式的旧物理学替换为新物理学,也推动了实验科学与新天文学引入奥斯曼帝国,但君士坦丁堡依旧顽固的宗教保守派势力导致致力于传播新科学的学者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如布珥伽瑞斯与忒欧托刻斯都最终选择定居俄罗斯。法国大革命的到来激化了保守力量对新科学的反对,却也使“希腊(语)启蒙运动”愈演愈烈,例如希腊启蒙主义活动家科德瑞卡斯·帕纳吉欧忒斯(Panagiotis Kodrikas, Κοδρικάς Παναγιώτης)1794年对丰特奈尔著作的翻译,就遭到反对日心说、坚持亚里士多德体系的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学校校长的强烈反击。最终,伴随着贯穿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民族国家革命运动,现代大学在爱奥尼亚、希腊、罗马尼亚等地纷纷建立,标志着欧洲科学在奥斯曼帝国昔日的疆域上终于实现建制化。

沈宇斌副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欧洲科学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播”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全球史研究论域,他尤其对耶路撒冷总主教克律珊托斯的全球知识旅行印象深刻,认为了解这段历史始末对于中国研究者而言是很有益的补充。
在提问与讨论环节,在场师生就南怀仁手稿的留存、宗教与天文学知识跨文化接受的关系、“希腊(语)启蒙运动”的概念界定、现代希腊科学史家如何看待本国科学史书写的连续性等问题向尼古拉耶迪斯教授提问,尼古拉耶迪斯教授一一作出了回应和补充。本次讲座在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撰稿:郑中天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