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作者:吴国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 点击下载: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独立精神”《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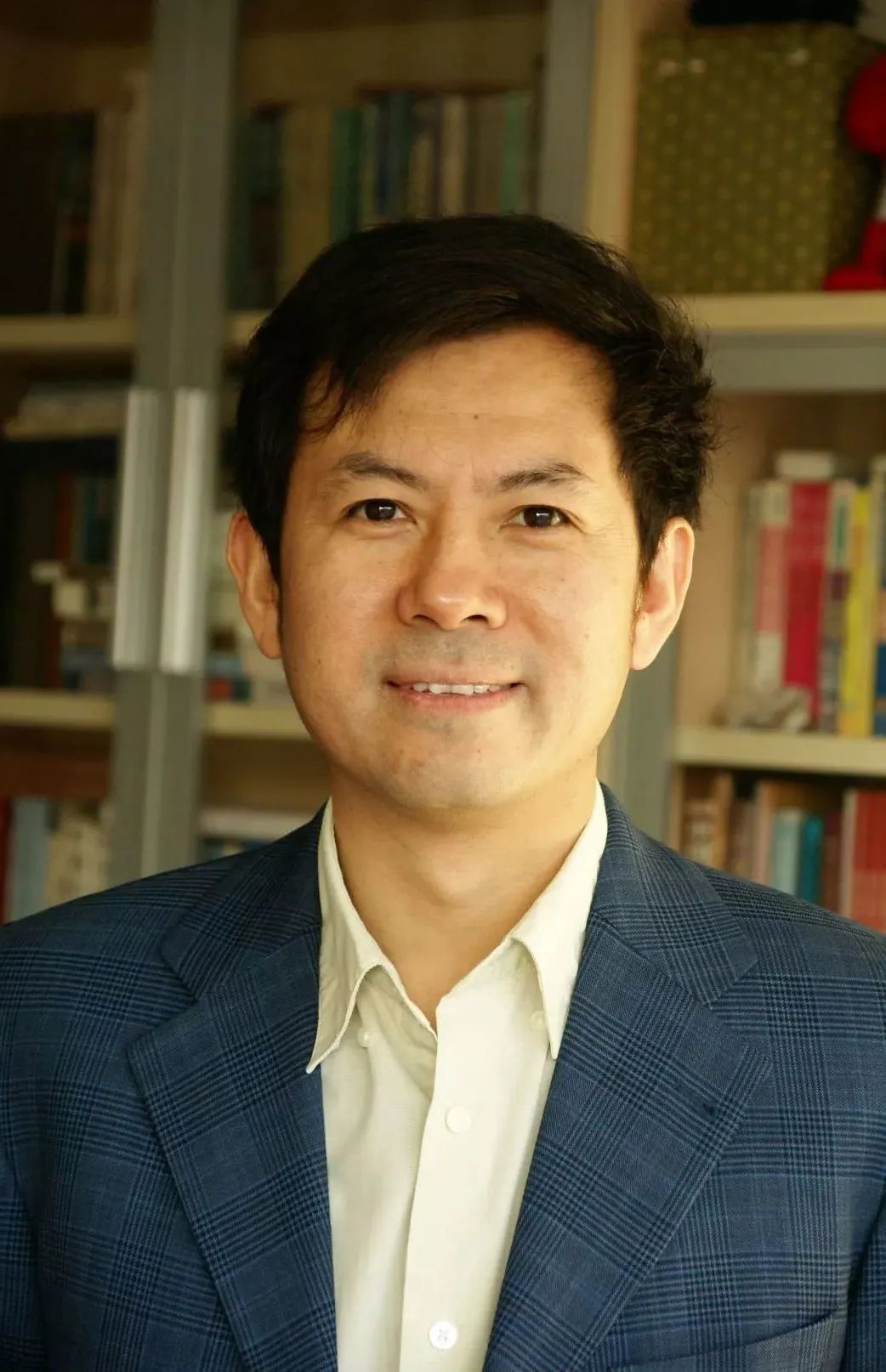
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
吴国盛
摘要
走向宇宙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它以宇宙同质观作为必要条件,以意志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充分条件。宇宙同质观源于中世纪晚期对人类认识有限性和认识视角的发现,人类中心主义则是中世纪晚期唯名论运动的直接后果。作为现代性之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引发了虚无主义,使物丧失“物性”,使世界不再有“意义”。安居大地是克服虚无主义的可行方案。“大地”不是表象化的“地球”。安居大地不是退守“地球”,而是重新找回“意义”。安居暗含了身体、位置、生态的重要性。重新发现身体、位置和生态,是克服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必要步骤。在“大地”观念指引下,航天与环保的矛盾可以被克服。
关键词
宇宙;大地;安居;宇宙同质观;人类中心主义;虚无主义
离开地球、走向宇宙深处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1609年,伽利略使用自己制造的望远镜发现月球表面有着地表一样的地貌特征。1634年,开普勒出版《月亮之梦》一书,幻想地球人与月亮人相遇交往的场面。1795年,天文学家威廉·赫歇尔在皇家学会《学报》上发文提出太阳上可以住人。19世纪后期,包括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翁、美国富翁洛韦尔在内的许多望远镜爱好者宣布在火星上发现运河。1969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在月亮表面留下人类的脚印。1977年9月5日,携带着地球人类文明信息光盘的旅行者1号发射升空,1979年3月到达木星,1980年11月掠过土星,2012年离开太阳系进入恒星际空间。进入新世纪,中国航天事业加快发展步伐:2003年10月,杨利伟驾驶神舟5号进入太空;2013年,嫦娥3号探测器在月球软着陆。今天,马斯克成功实现火箭回收、布置地球近地星链、计划开发火星,代表着这个时代最神奇的力量和最具创新的技术成就。宇宙航行是现代精神的体现,是科普写作和科幻文学永恒的主题。
固守地球、保护地球似乎是后现代的要求。奥尔多·利奥波德在1947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中提出“像山一样思考”“土地伦理”和“生态良知”。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控诉滥用杀虫剂导致昆虫鸟兽大量死亡,春天成为没有鸟叫的春天。1970年4月22日,全美开展环保宣传活动,成为第一个“地球日”。1972年6月5日—16日,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基调报告是《只有一个地球》,6月5日,后来成为“世界环境日”。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基调报告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同年,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保护地球生物资源制定《生物多样性公约》。此后,为约束温室气体排放,1997年12月制定《京都议定书》,2016年4月,175个国家签订《巴黎协定》。保护地球是新的时代精神,是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而且指向新的文明类型。
“走向宇宙”和“安居地球”是两种相互矛盾的人类意向。环境主义者与现代主义者之间形形色色的冲突都来自这种矛盾。如果人类的目标最终是走向宇宙,那么,保护地球最多只是暂时的过渡措施,并不具备终极的优先重要性。如果人类的目标是安居地球,那么,走向宇宙也只能是少数人的偶然冲动和冒险尝试,并不是全人类应该为之投入和努力的方向。走向宇宙派认为,节约能源、保护地球生态和生物多样性,都只是人类的技术能力不够强大的表现,一旦技术能力足够强大,能源问题、生态问题都不是问题。再说,地球也只是人类偶然乘坐的一个宇宙飞船,我们早晚会弃船的。航天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有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呆在摇篮之中”。安居地球派则认为,无论我们的技术如何发展,人类永远不可能离开地球,地球是人类唯一的永恒家园。
走向宇宙还是安居地球?这是我们时代最大的哲学问题。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走向宇宙和安居地球各自的深层思想根源、各自的正当性和局限性。本文对此做些探讨。
一、宇宙同质观
畅想宇宙、漫游太空、寻找“外星人”,其观念背景是宇宙同质观(cosmic homogeneity)。只有认同宇宙“处处均匀、各向同性”,我们才会相信我们的地球不是什么特殊的地方,宇宙各处都可以有我们人类熟悉的生活场景,甚至有类似我们这样的智慧生物,我们才能真的“走向宇宙”。宇宙同质观是走向宇宙的必要条件。
然而,宇宙同质观完全是一个现代观念。从希腊古典时代到文艺复兴时期,宇宙作为cosmos,是一个有限球状的、有等级差异的整体。正是宇宙的非同质性,构成了宇宙秩序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宇宙的等级首先体现在以月球天球划分的天界与地界之判然不同,其次体现在地界土圈、水圈、气圈和火圈的不同。天界永恒持久、没有变化,天界元素是单一的以太,天界运动的基本形式是匀速圆周运动。地界无物常住、变化多端,地界元素是土、水、气、火,地界运动的基本形式是直线运动。土水气火四元素不仅体现的是干湿性和冷热性的不同组合(干冷为土,湿冷为水,湿热为水,干热为火),而且也体现了重性、次重、次轻和轻性的不同,以及它们与地心距离由小到大的排布。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运动起源于潜能与现实的差异,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化即是运动。位置运动的前提是位置本身的差异性。如果此处与彼处没有本质的差异,运动就没有意义。物体运动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自然运动,一种是受迫运动。自然运动是运动的基本形式,受迫运动是对自然运动的干扰和反动。一个物体之所以有自然运动,是因为它尚未处在它应该在的自然位置,因而尚未达成它自己的现实性。趋向自己的自然位置,由潜能走向现实,是为自然运动。倘若空间处处均匀、各向同性,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运动就成为不可能的、无意义的。
牛顿作为现代科学革命的集大成者和全部现代科学的奠基者,完整地表达了宇宙同质观。在牛顿的自然哲学体系中,世界的基本要素是统一的物质和运动。天界和地界的二分被彻底打破,驱使苹果落地和月球绕地转动的是同一个“万有”引力。物质不再从实体和属性的角度去理解,而是还原为可以量化的“质量”;换而言之,所有的物质就其具有质量而言都是同质的,区别只在于拥有的质量多少。物和物之间不存在质的差异,只有量的差异。运动不再从潜能和现实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还原为空间在时间中的变迁,而空间,不再是能够影响物之为物的位置(topos),而是单纯、空洞、同质的几何空间。由于空间处处均匀、各向同性,因此,运动的要害不在于空间点的变化(空间点之间并无差异,因此,空间点的改变其实等于没改变),而在于变化的“方式”。单向的与时间成正比的均匀变化(即匀速直线运动)在本体论上等同于不变化(静止),并且取得了无须说明的优先地位,被称为惯性运动。
由于物体与空间分离,物体在空间中运动或者不运动,都不会影响到物之所“是”。反之,物体也无法改变空间(牛顿称这样的空间为绝对空间)。同样,物体和运动也相互外在、互不相干。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的惯性运动状态和静止在本体论上是一回事。运动也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那样出自物体自身(潜能向现实的转化)的内在要求,而是外在于物体的另一种物理性质。正如标定物质的是质量,标定运动的是动量、能量。了解了质量、动量、能量,就了解了宇宙的物理面貌。
走向宇宙的现代性冲动,以牛顿力学所表达的宇宙同质思想为前提。在牛顿力学指引下,航天事业快速发展。1968年阿波罗8号从月球返航途中,当地面控制中心问及谁在驾驶时,指令长博尔曼不无幽默但相当正确地回答说:“我想是牛顿在驾驶。”
哥白尼是打破宇宙异质观的重要里程碑。哥白尼革命的要害不在于把宇宙中心由地球移到太阳,而在于推动和助长了宇宙同质观。在现代早期的科学观念变革史上,宇宙同质观包含“天地无别”和“宇宙无限”两个逻辑蕴涵但又先后递进的观念。哥白尼出于简化行星天文学的技术原因让太阳代替地球成为宇宙中心,就必须让“地”球像“天”球一样做黄道圆周运动;开普勒三定律彻底把地球运动纳入太阳系诸行星的行列,实现了“地”之“天”化;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统一了自由落体、单摆、陀螺等地面运动与月亮、行星、彗星以及岁差等天体运动,实现了“天地无别”。哥白尼让地球的周日自转取代了恒星天球的周日转动,群星就不必统一镶嵌在天球上,就有可能散布在无限或无限定的空间中,这提示了“宇宙无限”。当然,哥白尼还不是宇宙无限论者。他的宇宙仍然是天球层层相套的有限宇宙。开普勒也不是宇宙无限论者。他虽然打碎了行星天球,让行星轨道成为椭圆,但仍然保留了恒星天球。然而,哥白尼天文学内在的宇宙无限论逻辑最终获得了兑现。伽利略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宇宙无限论,但明确否定了宇宙中心。类似地,笛卡尔把宇宙看成是“无定限的”。牛顿最终通过绝对空间的概念承认了宇宙的无限性。宇宙无限观借助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成为现代占支配地位的宇宙观。正因为此,科学史家柯瓦雷把现代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无限宇宙论是现代性最深刻的哲学基础。
宇宙无限论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首创,古代原子论者就已经主张宇宙无限。但是,原子论思想受到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主流科学思想的压制,未成气候。在12世纪—13世纪亚里士多德成为基督教经院哲学的学术权威之后,宇宙无限论当然继续受到压制,不可能在古典学术的复兴运动中被欧洲人自动接受。导致宇宙无限论脱颖而出的,恰恰是基督教神学的内在思想运动。原子论的复兴,其实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神学中独立获得了宇宙无限思想之后。
在哥白尼1543年《天球运行论》出版之前一百年,红衣主教库萨的尼古拉(1401—1464)在《论有学识的无知》中明确提出了宇宙无限观。这位影响卓著的中世纪晚期哲学家说,宇宙是一个“中心无处不在、圆周处处不在”的无限球体。半径越大,圆周与切线就越接近。如果一个球体的半径是无限的,那么,圆周就与切线合二为一、成了直线,不再是“圆周”了,所以,圆周处处不在。如果圆周成了直线,那么,就有无限多的圆心了,所以,圆心无处不在。这个无限球体的隐喻是将上帝的无限转移到作为上帝造物的宇宙之无限的关键点。
我们的感觉经验的确呈现给我们有限宇宙的观念。正像开普勒所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有限尺寸、离我们有限距离的东西。我们的感官无法感知无限。希腊人天球套地球的宇宙论非常适合人类的直观感受。很显然,宇宙无限的观念并不符合人类的经验常识。卡斯滕·哈里斯认为,宇宙无限的观念来自对人类视角及其局限性的发现。
人类有许多特定的认知视角,比如用眼睛观看(而不是像蝙蝠那样主要靠听觉)、位于地球上观看(太阳和月亮成为天空中尺寸相当的最醒目天体)、在太阳的青壮年时期观看等等。这是人类这种物种无法避免的处境。希腊人让这些特定的基于人类特定经验和常识的相对视角成为未经反思的优先绝对视角,就得出了包括地心说在内的一整套物理学和宇宙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特定视角的存在、本能地将自己体验为中心,就容易把地心宇宙论看成是客观真理,把“特殊偶然”直接当成了“普遍必然”。库萨的尼古拉称之为缺乏“有学识的无知”,弗兰西斯·培根后来称之为认识论上的“种族偶像”。希腊人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够借助于理性达成事物“本身”的“真理”,却未意识到人类理性固有的视角性,被基督教神学认为是一种傲慢之罪。
基督教神学基本教义之一是亚当堕落(原罪说)。由于始祖堕落,人类因而丧失了原本完善的认知能力。13世纪—14世纪轰轰烈烈的唯名论运动,高扬上帝绝对全能、绝对自由的思想,从而揭示并强化了人类视角的存在。库萨的尼古拉继承了唯名论运动的基本精神,在认识论上极大地强化了上帝与人之间的绝对鸿沟,贬低人类的认识能力,明确地指出人类认知的有限性、视角性。他在主张地球运动时说:“这个大地确实是在运动,虽然我们看来它似乎是静止的。事实上,只有对照某些静止的东西,我们才能探测到任何事物的运动。”他引入的运动相对性概念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他紧接着说,“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道理,为什么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在大地上,在太阳上,或在另外一个行星上,都总是有这种印象,认为所有别的东西都在运动,而他自己却处于一种不动的中心里;他必定总是要这样来选择其天极,这些天极按照他所在位置是太阳、地球、月亮、火星等等而各不相同。因此,将有一个宇宙体系(世界机器),它的中心可以说是到处都在,而它的圆周则哪里都不在,因为上帝乃是它的圆周与中心,而他正是到处都在又是哪里都不在的。”
意识到人类视角的存在,就同时暗示、进而实现了对这种视角的超越。卡斯滕·哈里斯称之为人类思想进化的“视角原理”。在《有学识的无知》中人类的视角被揭示出来,同时伴随着关于无限宇宙的暗示和想象。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当下的宇宙图像只是我们位于地球上所见,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人在火星上甚至在遥远的恒星上可能见到不同的景象;我们可以想象火星或恒星观察者的宇宙图像,意味着我们和其他观察者之间在获得宇宙图像方面有共同之处,这些不同的宇宙图像都有其平等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宇宙同质观念。逻辑上,就导致了宇宙无限观。库萨的尼古拉一步到位,借用出自伪赫尔墨尔主义的无限球体隐喻,直接演绎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柯瓦雷因此“不得不称赞库萨的尼古拉宇宙论思想的大胆和深刻”。
宇宙同质只是人类“走向宇宙”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人类有强烈的愿望并且自信有足够的能力走向宇宙。提供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充分自信的,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令人惊奇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中世纪后期与宇宙同质论同时浮现出来的。
二、人类中心主义
宇宙同质论基于对人类有限性、视角性的发现,似乎必然伴随着对人类的贬低。叔本华、尼采都认为,哥白尼对地心说的拒斥,必然导致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拒斥。时至今日仍然有这样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哥白尼的日心说将人类从宇宙的中心位置驱离,降低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打击了人类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紧随哥白尼之后的还有达尔文和弗洛伊德。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本人,还可以追溯到1882年法国生理学家波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在达尔文去世后发表的悼词“达尔文与哥白尼”。罗素主张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应该恰当地称为“托勒密式革命”,表明他认可哥白尼日心说贬低了人类地位的说法,而托勒密倒是维护了人类的主体性。但是,历史学家柯林武德驳斥过这样的说法,认为日心说并没有贬低人类地位。人类居住地的狭小微不足道,丝毫不意味着人类地位的微不足道。情况似乎完全相反,与宇宙同质论、宇宙无限论、人类有限论相伴随出现的,恰恰是人类中心主义。整个现代性就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之上。
为什么在唯名论运动强化了人类的有限性的时候,却不经意间促成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史家汉斯·布鲁门伯格在《现代的正当性》中,最早揭示了从唯名论的神学绝对主义到人的自我捍卫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唯名论过分高扬上帝的绝对全能,使得上帝显得喜怒无常、世界秩序荡然无存、得救毫无希望,人类不得不求诸自己,以重建世界的秩序和人生的意义。哈里斯用视角原理来表述这种人类的“逆袭”现象,即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视角性的时候,同时也就意识到了某种超视角的存在;当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同时也就提醒自己去超越这种有限性、发现自身的无限性。追求这种超视角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近代思想一方面是贬低人类“感官”,认为正是它妨碍了我们获得真理、接近实在;从哥白尼到伽利略、笛卡尔,对眼睛的不信任是现代早期实在观的鲜明特征。另一方面,近代思想高扬人类“精神”,认为它可以超越感官的局限,某种意义上可以像上帝那样获得真理、接近实在。现代思想的这种双重性,展示的就是视角与超越的双重性。
双重运作的主要方案是强调人类的精神性存在:人之为人不在肉身而在精神。从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1260—1328)开始,中世纪后期关于纯粹的无身体的“心灵”的思想成为经院思想的一大主题。帕斯卡的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表达的也正是这种人类的优越性。人类的精神性,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神性或类神性。
这种精神性存在包括知、情、意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在“情”的方面,就是“美学”的发明——美学并不是一个古老的学科,而是现代性的产物。人能够审美、体验“崇高”——既包括自然界的崇高,也包括人类自己的崇高,表明人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物。登山运动、飞行表演,渴望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都属于这个意义上的崇高体验。审美和体验崇高的能力,展示了人类自我超越的能力。今天,作为审美主要战场的艺术经验被认做人类自由的真正体现,现代艺术家因而获得了古代从未获得的崇高地位。现代艺术成为现代人性的高地。库恩说:“公众拒斥科学部分地出自他们的忧虑心情,因此他们通常是拒斥整个科学……公众拒斥艺术却是拒斥一种艺术运动而赞赏另一种艺术运动,”公众从不会拒绝整个艺术。
在“知”的方面,强调人类理性虽然是有限理性,但是它毕竟是上帝特别为人类创造的(其他动物不曾具备),因此与上帝的无限理性仍然是相似的。某种意义上,人类理性还是有可能接近上帝理性,能够理解宇宙的秩序。现代科学的开创者们大多在高扬人类理性方面不遗余力。哥白尼坚信人类理性可以发现宇宙奥秘,人类有能力追求真理。他和开普勒一样,之所以不接受宇宙的无限性,是害怕这种无限性会伤害人类理性获取真理的自信心。奥西安德尔为《天球运行论》写的匿名序言,表达的是唯名论思想所揭示的人类有限性——“谁也不要指望能从天文学中得到任何确定的东西”,满足于把哥白尼的宇宙模型看成是一种假说,而不是关于真理的揭示。但是,哥白尼主义者开普勒、布鲁诺,一眼看去就知道这不是哥白尼自己的意思。
笛卡尔缔造的人类理性升级版,为现代哲学奠定了基础。笛卡尔理性主义有两个彼此不无联系的方面:简单直观的理性与构造操作的理性。我们虽然受限于我们的肉身,只能获得一些视角化的知识,但我们也拥有不受视角限制的直觉能力,这就是对简单性质的直觉。简单性质有三类:一类是纯粹理智的如“我思”,一类是纯粹物质的如“广延”,一类是纯粹理智和纯粹物质共同的如“同一性”。对简单性质,我们可能理解也可能不理解,但不可能错误理解。这些简单性质本质上不是“可感物”,而是“可理解物”。数学正是关于这些简单性质的普遍必然的知识。人类因为有“我思”这样关于简单性质的思维能力,有数学能力,而成为认识论上的主体。和伽利略一样,笛卡尔都认定自然之书是上帝使用数学语言写作的。人类因为拥有数学直觉能力,某种意义上获得了认识真理的能力。
然而,如此这般的简单性虽然摆脱了感官的视角性,怎知不是人类心灵特有的虚构?弗兰西斯·培根正好有此担心,他甚至怀疑数学也只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虚构、一种“种族偶像”。为了回应培根的担心,笛卡尔提出了构造和操控的思想予以补充,以表明人类的确拥有追求真理的能力。他认为,我们可以根据简单性质将我们特有的感官视角重新“构造”出来,比如把颜色还原为不同波长的光波,把行星逆行还原为该行星与地球的相对运动,这就表明了简单性质的客观特征。进一步,笛卡尔把主体性由普遍数学转移到了机械制造能力。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制造出一个东西,才能说真正理解并且控制这个东西。笛卡尔后期迷恋自动机、迷恋构造世界和人体的机械模型,都是出于这个思路。
这就涉及人类主体性的“意”的方面。库萨的尼古拉早就提出了从“意志”角度为人类主体性辩护的思路。一方面,他一再强调有限的人类理智根本没有可能认识宇宙的真理,因为肉身的限制不可避免会产生有限的视角;另一方面,人有能力“创造”概念世界,就其作为此类“创造者”而言,人是第二个神。人虽然不能直接认识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但却能够认识根据自己的尺度所呈现的世界表象,即概念化的世界图景。笛卡尔继承和发展了库萨的思想。他说:“人的主要的完美之点,就在于他能借意志自由行动,他之所以应受赞美,或应受惩责,其原因也在于此。”“我之所以带有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相似性的,主要是意志。因为,虽然意志在上帝之内比在我之内要大得无法比拟……如果我把意志形式地恰如其分地对它本身加以考虑的话,那么我就觉得它就不是更大。”对笛卡尔来说,人类的理性与上帝理性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但“创造”的意志却使人类能够更接近上帝,甚至与上帝同一。
意志对于理性的渗透是现代理性区别于希腊理性的根本。人类能够理解的只有他自己能够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制造事物,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事物。“创造”不仅使“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产生真实的“控制”力量。人类因为拥有与上帝类似的创造意志和创造能力而成为人,创造的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
于是,“意志”的方面主导了“情感”和“认知”的方面。现代“思想”不再是希腊人的纯粹理性,而是一个再现和构造表象的意志活动。不仅笛卡尔的理性之中同时包含了直观理性和作为意志的构造理性,康德和黑格尔也都把理性看成是知识与意志的统一体。人不再看成是纯粹理性的存在,而被优先看成是意志的存在。笛卡尔甚至认为,上帝与人的差异只在认知方面,一个是无限理性,一个是有限理性,但就意志而言,人和上帝是一样的。
唯名论运动对人类有限视角的发现,反而推动酝酿了人类主体性。在唯名论高扬上帝的绝对全能而贬低人的“认知”能力之后,意志论的人类中心主义反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人类作为意志,世界就只能作为表象。人类能够认识到的也就是人类自己“制造”的表象。表象能力也就是概念“创造”能力,表明我们能够接近真理,但我们仍然只是把握到了我们能够实际有效把握的东西,并且以这些东西作为标准和尺度来理解世界表象。我们把握到的仍然不是实在本身,而是实在的那些容易被人类牢固把握的形式。我们追求的不是真理本身,而是真理的某种容易被人类牢固把握的“显示方式”。雅各布·克莱因深刻地指出:“17世纪所设想的‘普遍科学’并非对真理的呈现,而是发现真理的技艺。”现代科学不是在寻找真理,而是在寻找发现真理的“技艺”和“方法”。正如物理学家海森堡所说:“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中只面对自己,而不再有其他任何伙伴或敌人……在消除了所有可能的对手之后,人类不再面对任何敌人,我们面对的只有自己。”
这就引向了虚无主义。
三、虚无主义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是宇宙同质观。万物平等平权,“全同”粒子在“处处均匀、各向同性”的空间中的数学运动,成为基本的科学世界图景。质的拉平,使价值和意义不再属于宇宙本身。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限的宇宙之中,但从中得不到任何安慰和意义感。叔本华在《作为意欲和表象的世界》第2卷的开头就说:“在有无数发光球体的无限空间里,围绕着其中一个发光球体旋转的是十来个更小一些的反射着光亮的球体,里面是炽热的,覆盖着凝固了的冰冷的外皮;在这外皮上面,某一霉菌层孕育出了有生命的和有认知的生物。这些就是源自经验的真理、现实和世界。”民国学者吴稚晖不无赞赏地把这种宇宙观称为“漆黑一团的宇宙观”。帕斯卡早已发出“这无限空间永恒的沉默使我恐惧”的感叹,深刻地揭示了宇宙同质观所引发的虚无主义。
现代科学眼中的宇宙是冷酷无情的宇宙。过去一百年,借助理论和观测,我们关于宇宙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只是越来越加强了人类在宇宙中微不足道、无关紧要的认识。著名物理学家温伯格在他的名著《最初三分钟: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的结尾处,在以物理学家、宇宙学家的身份讲述了复杂而又精妙的宇宙创生故事之后,感叹说:“宇宙愈可理解,就也愈索然无味。”自然的去魅是虚无主义的深刻表现。
既然宇宙处处同质、目的中性、意义冷漠,人类为何还要“走向宇宙”?只有在展现人类“求力意志”的意义上才能为宇宙航行辩护。由于宇宙处处均匀,走向宇宙并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任何地方都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是,走向宇宙却能展现我们的力量、从而创造人类存在的意义,这是人类中心主义提供的内在动力和充分条件。一方面是无限宇宙的空虚、冷漠和无意义,一方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求力意志”,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体两面。它们相互映照。
但是,虚无主义不只体现在无限宇宙的空虚冷漠,也体现在人类主体的求力意志上。求力意志表面上看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即在无意义的宇宙中为人类的存在赋予意义。但是正如海德格尔所洞察到的,求力意志把人类自己表达为最高最后的尺度和标准,从自身出发来构造世界,这种“赋予”相反加强了世界本身的无意义,从而也加强了虚无主义。尼采的超人表面看超越了虚无主义,但实际上达到了虚无主义的极致,因为虚无主义的本质是,让世界在根本意义上丧失了“自身”。
海德格尔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本身就是虚无主义。用他的话说,虚无主义就是存在的遗忘,而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存在的遗忘。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上,物依据各式各样的最高实体而被理解成各式各样的存在者,物“自身”即物之存在则早已经被遗忘。在以求力意志为主体的现代形而上学中,物也只能根据求力意志的尺度和标准被理解成征服、算计和配置的对象。物丧失自身,是最深刻的虚无主义。
航天的确力量感十足。里根1982年6月在接见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第四次返航时,称航天体现了美国的开拓者精神,宇航员体现了“美国人仍有驯服猛兽的真正勇气”。许多热爱航天的现代人认为,向宇宙空间的拓展体现并确证了人类的求力意志本质,从而体现并确证了人性,因此,走向宇宙或许甚至可以看成是人类的“返乡之行”——人类来自宇宙,人类的故乡是星辰大海。
作为人性之“家”的究竟是“求力意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卡尔·萨根作为航天运动最有影响的鼓吹者,也是地外生命甚至地外智慧生命的坚定信奉者,虽然直到他1996年去世,航天活动都没有发现任何地外生命的迹象。对“走向宇宙”的鼓吹者来说,一定要相信宇宙间处处有“生命”。17世纪开普勒讲述的关于月亮的故事,首先是地球人与月亮“人”的故事。19世纪对火星轰动一时的关注,是号称发现了火星“人”建造的火星运河。走向宇宙其实是继续我们在地球上已然熟悉的生活。如果茫茫宇宙除地球外处处都是不毛之地,那我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离开地球?我们花在航天上的力气和聪明才智——那能够证明人类伟大主体性的东西——就不能用在改善地球上人类的境况吗?但正因为在那远离地球的宇宙深处,也有生命存在,因而也可能成为人类的新家,就如同新大陆成为欧洲人的新家园一样,走向宇宙才是值得追求的。相信存在地外“生命”暗示了,“家乡”与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走向宇宙也是某种形式的寻找“类地”“家园”。
四、安居大地
希腊理性主义造就了“地球”概念。1959年,探索者6号第一次拍下了地球作为球体的照片,1961年,尤金·加加林作为人类第一次见到地球作为球体的全貌,但在此之前两千四百多年前,希腊人以其高超的理性思维能力遥遥领先地确立了地“球”概念。当然,地球概念的确立也依赖天球概念以及图像化的“宇宙”概念。地“球”以其对几何形状的强调,成为世界图像的一个显著标志。我们一谈起“地球”,便容易陷入表象化思维方式之中,陷入那种根本上的虚无主义境地。地球概念是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论优位观点的产物。我们现在需要重新思考我们脚下的大地。脚下的“大地”,而不是我们只有仿佛飘在空中才能见到的“地球”,才能把我们从认识论优位的形而上学传统中解放出来,思考我们生活的意义。
“大地”概念唤醒了人的定居本性,而大地即安居之所。打量和静观外界只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派生的方式,既不是全部的方式,也不是优先的方式。从希腊语源上讲,理论(theory)即静观(theorein)。理论优位的世界观是希腊人的发明,主要依据“看”来建立与世界的关系。现代人通过发现“看”的相对性,部分解构了“看”的优先地位,但依据“意志”来建立与世界的关系也被尼采所解构。一个世纪以来通过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印证了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困境。人类需要寻找新的存在维度:基于“位置”的“安居”。
希腊科学—哲学起源于好奇心,而好奇必然带来“脱位”或“越位”,即对安居的一种动摇。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由于仰望星空而不慎跌入深坑,亚当夏娃出于好奇心而吃禁果,都是对这种“脱位”的一种生动记录和隐喻。西方科学由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再由哥白尼革命引发对地球的离弃,一路狂奔,兑现了好奇心带来的无家可归和流离失所的命运。越位即弃家。
安居暗含了身体、位置、生态的重要性。重新发现身体、位置和生态,是克服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必要步骤。
身体提供方位,为人类定“位”。上下的概念起源于人类的直立行走状态,远近的概念起源于身体的有限性。只有有限的东西才能区分远近,无限则与一切事物保持相等距离。宽敞辽阔与自由的概念相伴随,也是因为身体能够受限。缺乏身体我们甚至无法理解自由概念。最基本的自由就是身体的不受限制,剥夺自由首先是剥夺身体的自由,但不受限制以身体能够受限为前提。
“位置”(place)被“空间”(space)取代,是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一个重要标志。希腊人只有位置(topos)概念而没有空间概念。拥有位置是存在的基本样式。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任何事物必然存在于某位置,占据一个地方。”位置揭示的是物与物之间的“依存”关系。亚里士多德的位置理论包含着“包围理论”和“自然位置”两个方面。包围理论说的是,一个物体的位置由包围它的东西来规定,这体现的是物物相依而存在,物不可能独自存在。自然位置理论说的是,一个物的本性(自然)决定了它的位置,如果它不处在它的本性为它规定的位置,那它就有一种出自本性的冲动,要回到这个独独属于它的位置。自然位置理论表明,位置也决定了存在者的存在状况:处在何种位置决定了一个物之物性的完善程度,只有在自己的自然(本性)位置才达到物(之本)性之完善。
笛卡尔的自然数学化理想把物质的本质还原为几何广延,牛顿则接过了剑桥柏拉图主义的绝对空间概念,他们共同造就了现代空间概念的支配地位。位置从此变成了空间的一种派生的局部概念,成为某种抽象空洞的地“点”。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强化了时间和空间的先验地位,而“位置”被全盘放弃。柯瓦雷总结说:“我总是说,近代科学打破了天与地的界限,把宇宙统一了起来。这是对的。但我也说过,这样做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它把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于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几何学在其中具体化的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
失位是虚无主义的典型症状。人丢失自己的位置必然带来错乱,丧失方向和目标。人类是动物,因此需要不断改变自己的位置,从而处在运动之中,但改变位置的前提是拥有位置。一个位置或令人不安、或单调乏味,已经或即将丧失其“位置性”,我们就寻找另一个位置。我们通过运动来恢复我们的位置性。如果我们根本上不拥有位置,运动的意义何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运动呢?
是空间先于位置还是位置先于空间?身体的介入就必然支持位置先于空间。空间提供一览无余的表象,而位置则提供无穷无尽的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知识。位置不仅提供广度、深度、高度,还提供温度、强度、力度。清新与污浊、健壮与虚弱、心跳与宁静、血气方刚与垂头丧气,都由位置—身体而来而无法还原到空间。希腊人的土、水、气、火四元素和中国人的阴阳五行知识,都来源于位置,来源于站立在大地之上的生活经验。
生态(ecology)的词根eco在希腊语中即“家”(oikos),生态观念就是居家观念。生态学的基本定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规律: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独自存在。海德格尔提出人的“在世存在”结构,其实就是生态结构。“在世”存在的“世”,就是“位置”,就是“家”。他后来所说的“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其实也就是“在世存在”。“世界”也罢、“大地”也罢,都是安居之所、人类的位置。
走向宇宙不一定能够克服虚无主义,返回大地才是正道。但是,返回大地并不是在表象意义上由太空回到地球——仿佛人类主体在航天上一无所获只能回头继续盘剥地球,而是回到安居状态。海德格尔称这种安居状态是天地人神的四方会合。这里,天空既不是单纯的几何图案,也不是无限的同质空间,而是安居的内在要素。星空写满了人类内心的渴望和冲动,飘满了作为精神指引者的动物和神灵。天空造就了人类心灵,维系着精神的丰盈。长久不仰望星空的人,会削弱方位感和灵敏度,有如久坐不动的人会导致体能下降。更不用说,挑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现代人身体机能的普遍失衡。在现代时间技术和空间技术支配下忽略与天空开展日常对话的现代人,心理必定是不健全的。仰望星空具有心理治疗作用。
在天地人神的四方会合中,“敬畏”是最重要的情绪。敬畏基于对自身有限性的深刻领悟。敬畏也把天地人神的四合安居作为生命意义之神秘而又永不枯竭的源泉。它暂时中断理性思考,向神秘力量屈服,但是它会让人更有创造力,让世界更新鲜、更兴味盎然。敬天畏地,使人类身心更健康。
令人惊奇也是令人欣慰的是,凡是登上过太空的宇航员都带着对地球的深深依恋和更强烈的保护地球的愿望回到地球,他们往往更加关注和支持环境保护事业。航天打动公众的,除了发现宇宙的壮美,还有发现地球这个蓝色星球的娇嫩,以及对地球摄人心魄的敬畏感。即使没有上过太空的普通人,在看了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无论是蓝色弹珠(blue marble)还是暗淡蓝点(pale blue dot)——后,都无不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神圣感。海德格尔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在1966年答《明镜》周刊记者的采访时说:“当我而今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惶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他的情绪似乎有些过激了。即便我们登上了太空,也不意味着我们和大地的关系只有纯粹的技术关系。事情似乎是,我们越是有能力走向太空,就越是热切地回归大地,向往安居。某种新地心说正在回归。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理性主义在基督教世界的复兴,同时触发了唯名论运动。唯名论运动高扬上帝绝对全能绝对意志的思想,揭示并强化了人类有限的思想。人类有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认识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这种无能首先表现在感官介入引发的认识偏差,弗兰西斯·培根称之为“种族偶像”。哥白尼以日心说代替地心说,所要处理的或许是数理天文学中的技术细节问题,但必定要把运动的相对性从而观察者的相对性问题突出地提示出来。运动观察者的相对性和平权性遂成为现代物理学的第一原理(伽利略原理或哥白尼原理)。认识到人类在认识上的局限性,同时就触发了为人类主体性辩护的非认识论路线:人类越来越多被看成是一种像上帝那样的意志的存在。从笛卡尔开始,经过康德、黑格尔直到叔本华、尼采,意志成为人类主体性的核心。尼采称这种主体性为“求力意志”。在求力意志主导下的人类认识,以数学的方式来描绘世界图像,追求对事物的控制和征服,形成了现代求力科学。现代人类通过张扬意志而自我确立,但却遭遇意义危机。在被摊平了的数学化的同质宇宙中,物不再有魅,全是僵死的全同粒子。在求力科学蒸蒸日上、引爆了核能量、登上了月球的20世纪,同时又触发了安居大地的意识,在理论理性和求力意志之外,提出了人类存在的“安居”维度。





